微信公众号2022年06月17日发布
一份留存至今的近代报刊和许多其他文物一样,某种程度上以其物质性成为一段历史跨越时空的见证。它最早便作为密集信息的载体诞生,汇集自天南海北、街头巷尾的新闻杂笔如同查探当时社会生活的索引,成为历史学家透过迷雾认识曾经人、事、物的提示。
近年来,近代报刊数字化工程进展殊大,许多“不解之谜”在学者对浩如烟海的近代报刊文章的不懈诠索下找到答案。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祝淳翔从戈公振《中国报学史》中提及的袁世凯称帝前后“假《时报》事”着眼,以一篇500字杂记为关键线索,向同时代人笔下寻访该杂记作者“虎厂”的身份与经历。从传闻到报纸一角再到各类时人笔记,刊登于我馆馆刊2021年第2期的这篇文章用精彩手法揭晓了“虎厂”隐藏在二字斋名后的人生,在此分享此文,共同领略近现代报刊研究的魅力一角。
近代新闻史上有一则传闻,流传甚广,脍炙人口,大致是说袁世凯称帝前后,有人制造虚假新闻欺瞒袁氏,以售其奸,史称“只供一人阅读的报纸”。时至今日,这一传说已衍生出各色版本,其中学界较为认同的,源自192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戈公振新闻史名著《中国报学史》;也有人援引张静庐辑注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》中戈氏长文《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》,实则同样节录自前述戈著。
戈公振在序言中提及此书缘起,称1925年夏国民大学成立,请他去讲“中国报学史”,他认为报学(journalism)在欧美都算是新颖学科,在中国更是“无成书可考”,没办法,只得“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,附以己见,编次为书”。
假报事件便是一则掌故,见于书中第五章“民国成立以后”之第一节“两度帝制之倏现”,提及改元洪宪后,上海各报如何应付,并引“近人虎厂杂记”言及假《时报》事,作者就此评论说:“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,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。”
“虎厂杂记”究竟为何种资料,令人倍感好奇,或许出自某张报纸某人的专栏,然而民初报纸浩如烟海,且旋起旋灭,能否留存至今都是个问题。即便近年来,近代报刊已被大量数字化,的确嘉惠学林,惜索引未能同步跟上,亦造成问题。这两大原因,便导致这一谜题历经多年,依然无解。
说来也巧,最近因为研究有着“东方卓别林”之称的徐卓呆,寓目一篇小报文章,即王寿富《东方笑匠徐卓呆》(刊《社会日报》1930年11月13日),谈及“从前小申报上,最多厂字派的同文,什么龙厂、虎厂、人厂,他(指徐卓呆)也瞎轧闹热,署了一个‘狗厂’”(这里的“厂”是旧时文人斋名,是庵、菴、盦的简笔异体字——引者注),令笔者茅塞顿开:《小申报》是席子佩创办的《新申报》副刊,遂利用抗战文献平台,逐日浏览,很快就在1922年12月14日该报找到了那篇《虎厂杂记》,内容与戈公振所引大体一致,唯个别字眼略有差异,今录文如下:

▲《虎厂杂记》(《新申报·小申报》1922年12月14日)
筹安时代,京中各报,慑伏于权力之下,咸一致拥戴。惟《顺天时报》颇多讥讽不满之词。然此报为日人机关,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,宜其有非难之声。故时人亦不重视之。惟上海各报,除薛大可组织之《亚细亚报》(《亚细亚日报》——引者注)外,所持论调,颇为国人所注目。及民四冬月,项城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,曩时部中即通令各省一律遵用。上海各报以格于禁令,勉强奉行,乃以近于滑稽之手段,改民国几年为西历纪元几年,更于西历下,别刊“洪宪元年”四小字,字绝纤细,读者苟不察,几不能见,其用心良苦矣。盖若不刊“洪宪元年”,销场只及上海一隅之地,不能普及全国,而邮局亦未能为之代递也。项城在京中所阅上海各报,皆由梁士诒、袁乃宽辈先行过目,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,皆易以拥戴字样,重制一版,每日如是,然后始进呈。项城不知也。一日,赵尔巽来谒,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,命侍卫延之入,寒暄毕,赵于无意中,随手取《时报》一纸阅之,略一审视,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。项城奇之,询其故。赵曰: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,然此固明明为上海《时报》也,故以为异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,阅竟大震怒,立传乃宽至,严词诘之;乃宽竟瞠目结舌,觳觫而不能对。
文中民国“几”年被手民误植为民国“元”年,诚不可恕,因洪宪元年相当于民国五年,报上的纪元不必回溯至民国元年。
然则虎厂又是何许人呢?亦值得探究。今查及杭州已故集邮家钟韵玉(1907—1996)的短文《〈新申报〉副刊别署热闹》(收于顾国华编《文坛杂忆初编》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,卷三),中略云:“上海永安公司天韵楼游艺场日刊主编王瀛洲于1926年邀余作助编,其时江红蕉在《新申报》编副刊,文友毕倚虹、赵苕狂、张四维、徐卓呆、姚苏凤、徐虎侯、庞京周、张士杰等时在天韵楼日刊编辑室茶叙,庞、徐两人兴之所至,随意写作小品投《新申报》,庞署名龙厂,徐称虎厂。”按天韵楼日刊即《天韵报》,创刊于1922年4月15日,报名多变。看来年深日久,钟氏关于时间的记忆略有偏差。又及,钟韵玉还在《杭州历史丛编·文化艺术卷》之《杭州早期文艺报刊》中提及“徐虎侯”:“‘卢齐战争’后,在上海汉口路145号出版《绿痕》旬刊,由张士杰助编,4开一张,内容为散文、杂作、掌故、漫谈,由胡同光插画。执笔者有张四维、钱化佛、王瀛洲、丁福保、胡悲天、郑正秋、庞京周、徐虎侯、魏墨怜等,共出版12期。”然而当调阅《绿痕》逐页翻找,未能找到“虎厂”署名,类似的只有“伏虎将军”,也不知是不是同一人。
在20世纪20年代《申报》外埠新闻上,多次见到宁波警察厅长徐虎侯,此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文人聚会的场合中。不禁令我怀疑钟先生的记忆也许又一次发生了淆乱。有趣的是,1925年第4卷第12期刊有范烟桥的一篇长文《徐卓呆的滑稽史》,回忆徐氏在《小申报》上署名的滑稽史时,他写道:“当庞京周闹着龙厂,徐☐☐闹着虎厂的时候,卓呆就夹蚌炒螺蛳似地闹着狗厂……”看来虎厂确实姓徐,唯名字未必是虎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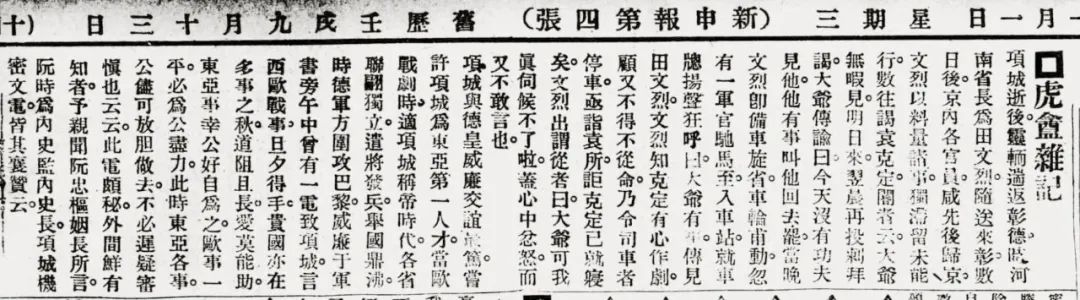
▲《新申报·小申报》于1922年11月1日刊载的《虎盦杂记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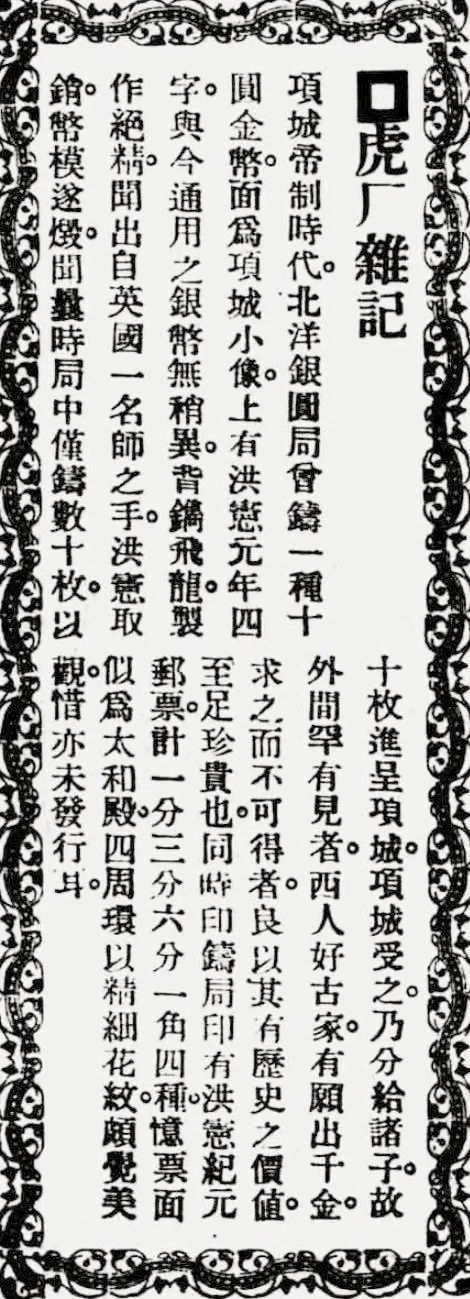
▲《新申报·小申报》于1922年12月15日刊载的《虎厂杂记》
只得继续翻报,发现1922年10月28日《虎盦杂记》在报上首度面世时,编者“小记者”(即严谔声)撰有推荐语:“今天所刊的虎盦杂记,是记的梁鸿志和杨度的轶事,我们从没听见过,请读者注意。”因事涉狎亵,不值一提。几天后的10月31日,“小记者”再度预告:“虎盦杂记,又寄来两则,都是讲的洪宪故事,很为确实,明天可以登出。”果然,次日的《虎盦杂记》谈及袁世凯与德皇威廉交谊甚笃,欧战剧烈时,恰逢“项城称帝时代,各省联翩独立,遣将发兵,举国鼎沸”,威廉修书一封寄给袁氏,说“西欧战事,旦夕得手,贵国亦在多事之秋,道阻且长,爱莫能助。东亚事幸公好自为之。欧事一平,必为公尽力。此时东亚各事,公尽可放胆做去,不必迟疑审慎也”。文末并透露了消息来源,“予亲闻阮忠枢姻长所言,阮时为内史监内史长。项城机密文电,皆其襄赞云”。
11月6日的《虎厂杂记》写袁世凯喜爱的子女中,三姑娘“名叔祯,性豪爽,无闺阁气,府中遇有外宾茶会聚餐,项城尝携之出,周旋于尊俎之间,行举中礼,后归皖人杨毓珣,实予作伐也”。吐露了关键的身份信息。
更早之前《新申报》刊有两张袁寒云客串出演的京剧剧照,分别为《黄鹤楼》与《群英会》,合作者中反复出现一个名字“徐南虎”,令我眼前一亮:此人既姓徐,名字中又带个虎字,八成就是虎厂吧。遂获睹杨吉孚(杨云史之子)《南虎轶事》(《上海画报》1926年129期),中谓:
徐君世翔,字慕邢,别署南虎,余表兄也。翩翩年少,倜傥风流,甫冠即喜冶游,北里中南北名花,鲜有不知南虎者,南虎亦尽识之,盖徜徉于花国者廿年于兹矣。君面如冠玉,态度文雅,有“特别照会”之称,观其玉手纤纤,朱唇皓齿,大类女郎也。
南虎与寒云、倚虹交至笃,北居则与寒云时相过从,南居则与倚虹朝夕聚晤,去岁倚虹组织《上海画报》,南虎亦赞助之一人,其后倚虹约君编纂,久之欲月以二百金为寿,南虎不可,曰:得酬不能自由,顾当尽力分劳也。其磊落如此。
南虎与杨毓珣为异姓昆季,去岁杨来苏,曾一度为杨之秘书长。
直奉既和,君辗转入吴孚威将军幕,是影故服戎装,为最近在汉所摄,此后特别照会,当改为戎马书生矣。
此处再次提及徐氏与“杨毓珣”有旧,正与虎盦自述合榫。本文发表时,附有徐氏戎装照片一张,似又与伏虎将军署名发生了联系。

▲徐慕邢肖像(《律和声》1924年1月1日)
在《新申报·小申报》上,《龙厂谈荟》曾有“吾友虎厂好作打油诗”的话,今确能找到庞京周与徐慕邢的交游记录,如荀慧生《小留香馆日记》:辛未年(1931)三月廿七日星期四记道:“昨前两日庞京周、徐慕邢两次令于莲仙持柬来约吃花酒,均辞谢未往。”
徐慕邢家世煊赫,据称是杨云史内侄,杜月笙便是通过徐氏的牵线搭桥结识了杨云史。今知杨云史有妻徐氏,名檀,字霞客,安徽南陵人,为两淮盐运使、福建按察使徐文达之长女,1903年与杨云史成婚。那么徐慕邢便是徐文达的孙辈。也正是拜这些人脉关系之赐,他不仅能在早年间担任徐世昌总统府秘书(范绍增口述、沈醉整理《关于杜月笙》),还在以后与北洋军政要员来往频密。而杨云史的女儿曾嫁与毕倚虹,因此毕徐之间亦是姻亲,南虎便经常无偿替毕氏主持的《上海画报》《晶报》供稿。
徐氏与袁寒云年龄相仿,情同手足,一起吃饭看戏之余,兼有诗词唱酬。后者的《辛丙秘苑·豹龛诗余》里有一首《贺新郎·调慕邢》,即写赠徐氏续弦事:“炎海清凉处。点酥娘、歌传皓齿,诵听灵赋。琢玉人间都羡取,休怨东风似妒。憔悴甚、空量缣素。一瞥惊心舒怨黛,尽无言有梦翻如故。弦可续,意难住。 芳时几逐春来去。看匆匆、明珠乍晦,金丝重度。玉马应随鸳枕系,省识青绳易误。人月静、无尘初步。却愿披云轻拂袖,纵连城不易倾城顾。君莫负,桃花渡。”
徐南虎非但是京剧票友,而且在1923年10月25日与张啸林、杜月笙共同组织律和票房,徐任副社长。此票房成员最多时达千余人,是旧上海票房规模最大的一家。

▲律和票房正副会长合影。左起:徐慕邢、张啸林、杜月笙(《律和声》1924年1月1日)
此外,徐氏还是著名集邮家。1922年11月初的《小申报》上有他征求邮票的启事:“如有前清及袁世凯、孙文、徐世昌像纪念邮票及去年发行之飞艇邮票见让者,当以新出各种书籍为酬,或现金亦可,函寄上海葛罗路十二号交徐慕邢收。”在《余之集邮谭》里,徐慕邢忆及早年集邮史:
余集邮开始远在民国三四年间,时方宦游北平。东安市场鲁人杨瑞年者,以买卖邮花为业,偶过其处,驻足而观,不觉好奇心油然而动。乃选购色泽鲜艳之西邮怀之而归。久之以不谙西文,更不辨国籍,似了无兴趣,遂幡然改变作风,大量购置前清各项分、角、元数等票,不论新旧,广事搜罗,先后购入者约有十余万枚。归而分类编排,盛到匣中,五彩缤纷,朝夕把玩,引为乐事。然所费亦不过数百元而已。朋侪皆讥余以有用之钱掷诸虚地,余亦一笑置之。时国内集邮者如凤毛麟角,寥若星辰,既无研求切磋之友,更少参考指导之书,故进步綦难,彷徨不知所措。有时遽尔灰心,即束诸高阁,不知所购之票,其中搀杂变体等票甚多,若各种中华民国倒印或无边漏齿及一分之壬字头者。嗣后略窥门径,始仔细逐一检点,皆成现时不可多得之品,而红印花各项加盖票,亦复应有尽有。……迨民国九十年间,袁寒云兄南下来沪,闲居无俚,喜集各项金银货币,久而生厌,继复开始集邮,异军突起,风气一开,更不吝巨资,搜求各票。余勉随骥尾,起而附和。一时市上较为名贵之票,价格骤涨,回溯寒云提倡之功,殊不可没。
又见陈志川在其主办的邮刊《国粹邮刊》之《海上邮人小志》专栏如此介绍他:“徐君慕邢,安徽南陵人,年五十有三,昔年曾宦居故都,与已故名邮家袁寒云君为莫逆交,与周今觉君亦为戚谊。集邮开始远在民国三、四年间,中途停滞者凡数次。迨八一三后,从新振刷,罗致珍罕之品无数。所藏大致完全外,更有副集新票一部。而红印花之收藏尤为君所深爱收集,方连、全格,复品甚丰。君秉性豪爽,有当其意者,皆不惜高价收买。”并且因收集红印花小一元新票,“不愧为战后国内唯一进步之大邮家”。(刊《国粹邮刊》第六期,1942年8月15日出版)
内容来源:《新闻出版博物馆》2021年第2期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