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信公众号2021年09月24日发布
《咬文嚼字》创刊伊始“一无刊号、二无编辑、三无发行”,郝铭鉴戏称其为“‘三无’刊物”。这本“‘三无’刊物”1999年正式拿到刊号,2000年开始交给邮局发行,依托强大专业的编校队伍和“以人为本、以质为魂、以用为上、以学为根”的十六字办刊方针,逐渐发展成为一本充满生命力的,在读者当中有信誉的优秀期刊。
郝铭鉴先生曾接受我馆采访,留下一段关于创刊、办刊的珍贵口述历史。今年4月,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,我们分享了这段口述历史的上半部分。

郝铭鉴先生与他创办的《咬文嚼字》,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学习与应用,在此选登《郝铭鉴谈〈咬文嚼字〉(下)》(郝铭鉴口述 林丽成采访整理)一文以续前次分享,在文字中感受先生曾经题写的赠读者寄语:"风雨阴晴君莫问,有书便是艳阳天。"

刊号 队伍 发行
正式亮相虽然成功,但这个刊物还是“三无”刊物。为什么叫“三无”刊物?一无刊号;二无编辑,一个编辑都没有,是我自己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编的;三无发行,社里面没有专职的发行帮我发这个刊物,要持久的话难度很大。这些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。一开始,我是向北京反映的,能不能给我刊号?许嘉璐非常热心,他多次跟总署联系,说这样的刊物是我抓的重点刊物,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刊号?但刊号管制很严。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李行健,一有机会也帮我呼吁要刊号。我们局里面也一直帮我跟北京要刊号。因为没有刊号,我们一开始都是称第几辑,不是第几期。有一次,总署的副署长梁衡找到我,因为他负责刊物整顿,他说刊物还是要继续办,等到有机会我们会考虑刊号问题。就这样,这个刊号的机会等了5年,从1995年到1999年。1999年突然通知我到北京新闻出版总署开一个会,上海去了两家。这次会议是解决刊号问题的。
注:经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档案,1998年7月16日,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向新闻出版署行文:关于《咬文嚼字》申请刊号的请示[沪新出(98)期字第034号];1999年3月11日,新闻出版署行文批复:关于同意创办《咬文嚼字》的批复[新出报刊(1999)226号]。由档案还知,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向新闻出版署申请的是16开本刊物,新闻出版署批复的也是16开本刊物,但《咬文嚼字》始终保持标准32开本,这也体现了郝铭鉴坚持的办刊宗旨:有内容、有格调、有气场的小刊物。
在总署的那次刊号会上,李岚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门找到我,他问我,你的刊物到底办给谁看?我的刊物读者对象非常明确,编辑、记者、校对、广播制作人、节目主持人,我告诉他是这五大类人。他说岚清副总理做了一个调查,全国的语文刊物量是不少的,特别是针对学生的,已经过量了。为什么给你们这个刊物一个刊号呢?因为你们不是针对学生的,你们是针对社会的,岚清副总理建议你们增加两类读者,第一类是中学教师,第二类是机关里面从事文秘工作的人员。一个学生读了刊物,他的水平提高了,只是一个学生;如果是针对教师的,一个教师的水平提高了,就是一个班级的水平提高了、一个学校的水平提高了,它的作用、意义是不一样的,所以他希望你们一定要把教师作为你们刊物的读者对象。还有一类是文秘工作人员,现在的文件中出了大量差错,包括办公厅、国务院都有差错,提高文秘工作人员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,不仅关系到机关的工作质量问题,还会给全社会树立一个榜样。后来我们就调整了,由五类读者变为七类读者,而且把中学教师作为我们的首位读者。李岚清办公室的人告诉我,岚清副总理非常关心这个刊物,让署里面专门考虑。我们是1999年拿到刊号的,2000年开始正式交给邮局发行,这是刊物发展的转折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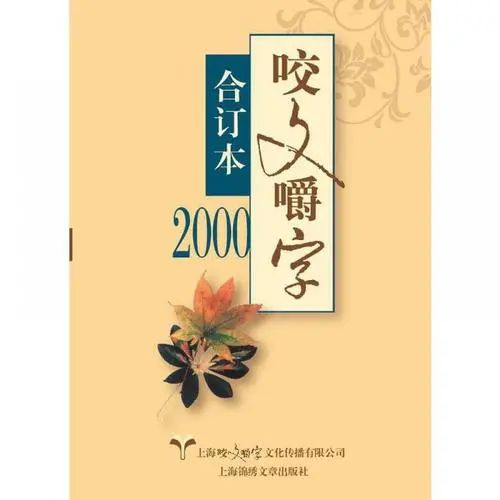
▲《咬文嚼字》2000年合订本
还有编辑队伍问题。没有编辑部,一个刊物要长期办下去,靠我一个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肯定不行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那时候也没有稿件,人家也不知道,所以我只能自己写稿,缺什么稿子就自己写一篇,刊物的一二三期好多稿子都是我自己写的。这样不行,一个刊物要正常运作,就要建立一个编辑部。
我先把在上海的、我自己知道的、有影响的语文界的人物请来做我的编委:一个是华师大的李玲璞教授,他是搞古文字研究的,我觉得他是不能少的;我的同班同学金文明编过《辞海》,又编过《汉语大词典》,我知道他的能耐,也请来做编委;第三位是我的老师、上海师范大学的何伟渔老师,他是专门研究语法的,而且他很擅长写普及类的文章,也请他做编委;还请了陈必祥,他是上海《中文自修》的原主编,非常熟悉中学教育,我们的刊物宗旨是要面向教育的,所以请他来做编委。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姚以恩,他是上海翻译家协会的,我们尽管是一个中文刊物,万一遇到外文类的东西,请他来帮忙解决。所以请了这五个编委。我们还请了顾问,罗竹风是语文协会的会长,又请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张斌教授,他是在全国有影响的,又是我大学里的汉语老师。张斌和复旦的胡裕树是几十年的学术搭档,所以再请胡裕树,又请了一位濮之珍,蒋孔阳的夫人,她是专门研究语言学史的。四位顾问、五位编委。后来扩大到东南亚,新加坡、马来西亚,还有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,这是后面的事情。


▲华东师范大学李玲璞教授(左),上海师范大学张斌教授(右)
顾问和编委都不做刊物编辑工作的。最初半年,我请我分管的理论室的林爱莲帮忙,我做刊物编辑工作,她作为责任编辑,把具体事务性的工作承担起来,我们两个人搭档,先把这个刊物撑起来。编辑人选,我首先想到当时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那里有很多精兵强将。我就通过金文明帮我到那里物色一下。半年以后,我从汉大把唐让之调来,唐让之的强项是音韵学,搞汉字音韵的,每个字读什么音,最后是他在那儿把关,这样的专业人才,不能不把他找来。还需要一些年轻的新鲜血液,所以就去复旦、华师大、上海师大,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拜访。复旦给我推荐了一个人,就是现在《咬文嚼字》的总经理王敏,我发觉这个人逻辑思维能力很强;华师大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黄安靖,现在是刊物的主编;还有一个人转了一圈,开始在郊区工作,后来又到《检察风云》,叫杨林成,这个人对文字也有兴趣。这么一来,《咬文嚼字》有三条汉子,都是科班出身,都是很强的。我再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找了一位韩秀凤,四个人搭成一个班子。现在看来,这真的是很强很强的一个班子,你看他们现在年纪不大,全部编审通过了,一个编辑部里所有人都是编审,三个人都是骨干。黄安靖现在是刊物主编,王敏当总经理了,杨林成被教育出版社挖走,现在是《语言文字周报》的执行主编。

▲《咬文嚼字》初创团队,前排左起:韩秀凤、郝铭鉴、唐让之;后排左起:王敏、黄安靖、杨林成(2001年)
即使有了他们,我还是强调这个刊物的校对工作比一般图书要加强,要找校对,而且这个校对任务是我们社里面一般的校对承担不了的。到哪里去找合适的校对?真的是苍天不负有心人,有一次在上海书展上,听到一个人在我身后不停地叨叨,说这本书的质量不高、那本书差错很多,我回头一看,是一个中年汉子。我问,你说差错很多,你看过没有?他说我怎么没看过?我看过才说它差错很多的。我说你还记得这些差错吗?他随手抽了一本词典,是古代人物词典,词典是很难发现差错的,他翻了两页,告诉我这里有一个什么错,我一看果然错了,又翻了一处什么错,我一看果然又错了。我想这个人才难得,我就问他,你是哪里的?他说我是铁路学校的教师,是铁路中学还是铁路党校我记不清楚了。我问他平时干什么,他说爱好看书,看各种各样的书,看到书的差错就把它勾出来。我告诉他,我现在办了一个刊物,就是要找差错的,你能不能做。他说这个事情最适合我,舍我其谁!这个人叫王瑞祥,我在上海书展上觅到的宝。我没想到,他对文字的敏感,真的是我们一般编校人员比不上的。他家里有三套《汉语大词典》,书房放一套,客厅放一套,厕所还放一套,随时在那翻;他家里把大百科全书全部配齐,真是入迷的。成了,我当时就约他做我们的特约审读。王瑞祥从《咬文嚼字》的特约审读开始做起,他的名气在上海一下子传开了,后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重点图书都找他审读,《大辞海》也找他,北京的《大百科全书》也来找他,都知道上海的王瑞祥可以把关的。有些刊物就固定地交给他来把最后一关,《新民周刊》等都是他做最后审读,成了审读专业户了。他不但速度快,而且眼光准,一眼扫下去就知道哪里可能出错,真的是一个人才。王瑞祥退休以后,更加有时间了,就专职做审读,辛苦是辛苦的,但他有兴趣。

▲郝铭鉴(左一)参加国际书展(1988年)
还有发行的问题。一开始《咬文嚼字》的发行是非常苦的,我反复找我们社的发行科,他们说这是用书号出的期刊,发行难度很大。我又开始找代理,代理的最大问题就是收不到款,书卖掉了,但款不给你结。最后只好自己做发行。当时我在上海找了10所学校,都是有我的同学在那儿工作的学校,让他们帮忙发行。譬如徐汇中学的校长是我的同学,他说每期可以发一千本;大同中学的语文老师答应帮我发,交换条件就是我得到大同中学去给学生上课。我一个人这么发,每期可以发掉一万本,比起有些刊物的起印数只有几千本,我相信《咬文嚼字》还是有市场的。但是我们只好控制印数,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发行力量。
后来发现我们的合订本市场很大,只要我一出合订本,马上有盗版,盗版的速度之快,你根本想不到。重庆有一家发行公司,说要包我的合订本发行,跟我说发行量20万;我一调查,实际印了40万,一个星期就全部发光了。合订本的量远远超出单行本的量,盗版还不计在里面。有一次我接到北京市工商局的电话,抓到一个盗版商,盗印了《咬文嚼字》,让我赶快派人过去一起处理。我问盗了多少,他们说,一房间全是《咬文嚼字》,已经把它封掉了,你赶快来处理,这次要狠狠地罚一下。我问怎么罚法,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罚他3000元。我当时一听就笑了,3000块,工商要留1500作为他们的执法成本,给我1500,到北京跑一次,机票都不够。我就找了天津的一个朋友来处理,《天津日报》有一个人是帮我们发《咬文嚼字》的,我就请他帮我处理这个事情。当时打击盗版的力度是很小的,所以盗版很猖狂。一开始的刊物发行,主要是靠合订本。1999年,有了刊号以后,发行就交给邮局了;但是合订本的影响还是大于单行本,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用合订本,觉得一年一本方便保存。
我们的刊物就是这样,从“三无”产品发展成一个知名品牌。
十六字办刊方针
一个刊物打得响还是容易的,站得住是更困难的。打得响,靠你想一个点子,比如“向我开炮”,一下子知名度就很高了;但是真正站得住,要靠你的办刊质量。怎么让刊物持续生存下去、发展下去?我总结为办《咬文嚼字》的十六字方针:以人为本,以质为魂,以用为上,以学为根。这十六个字是贯穿我们办刊始终的。
首先是“以人为本”,对你的读者要非常了解,而且要非常忠诚。不是让读者忠诚于你的刊物,而是你的刊物忠诚于读者,你要以你的服务让读者信任你、期待你、追随你。我们的读者,一开始是五类,后来变成七类,我们对自己的读者定位是很窄的。我们不像有些刊物,面对广大读者。这个广大读者,往往你心里的读者对象是不明确的,因为你不知道给谁看,我们是非常明确的,就是给这七类人看的。这批人的特点是什么呢?工作是非常紧张的,时间是非常少的,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的,但大部分人又是没有经过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的。他们的阅读,不可能是定定心心、正襟危坐、泡一杯茶坐在那儿的,而是见缝插针的。所以我们刊物的文章一定要短,我们强行规定48面的篇幅至少要发50篇文章,要让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完一篇文章。其次,这批人是搞语言文字工作的,他碰到的问题都是工作当中的问题,刊物一定要实在,不讲空的道理,针对性要非常强,看了你的刊物,就能解决他碰到的问题。还有,他没有经过系统训练,所以不能搞名词术语,讲了半天他看不懂。我们要提倡无障碍阅读,让他看得懂。譬如碰到一个很冷僻的字,就要注音,让他可以顺利地读下去,这就是为读者服务。我们非常明确,要尽可能地营造与读者的亲近感,不能跟读者拉开距离。从创刊开始,就用“我”“你”这样的称呼跟读者交流,用第二人称,让读者感到这是一种促膝谈心。要创造各种条件,让读者走进你的刊物。我们提出,来信必复,你只要来信我就给你回信,一开始我们是做得到的,到后来,来信量实在太大了。我不是吹牛,每年我自己写出去的信是几百封、上千封。在全国的刊物主编中,有几个主编能够跟读者保持这么一种联系?我觉得是很难的。而且我们后来又办了读者俱乐部,开设了热线电话,都是为了跟读者建立联系。这就是我说的一定要以人为本,你要时时想到你的读者们需要什么,就是要听读者想说的,说读者想听的。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到你做的正是他想要的。这就是“以人为本”的办刊方针。

▲郝铭鉴(左二)在“月亮神”报刊编校质量有奖竞查结果发布会上(1995年)
第二是“以质为魂”。质量是刊物的灵魂,绝对不能马马虎虎,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刊物。所以每审一篇稿件,至少要核对三种工具书。一般出版社是做三个校次,三校一读;我们是十个校次,我们有很多外聘的编审做刊物审读,通过增加校次来使刊物减少差错。即使这样的话,还有差错怎么办?开设专栏“向我开炮”,把创刊搞的活动做成一个栏目,专门纠正自己的差错。我举一个小例子,我们曾经搞过一个活动,叫“为城市洗把脸”,这样的活动,看起来好像只要看到一个差错,拍一个照片、写一段文字就可以了,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。所有读者提供的差错,我们的编辑都要去实地考察,要去核实,不要因为读者的理解产生问题。比如有读者反映,故宫里面有一个具服台,皇帝祭天时要到这里换衣服,换上蓝色的衣服,这里有一个说明牌,把蓝色的蓝写成兰花的兰,这当然是一个差错,读者把牌子拍来了。我们想想故宫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差错,专门派编辑去核对,果然那个牌子还在,蓝色的蓝写成兰花的兰,错了。照理说,我们指出它的差错就可以了,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差错,对读者来说受益不大,缺乏知识含量。所以我就对这个编辑说,为什么皇帝祭天要到这里换衣服,为什么要换蓝色的衣服,你能不能找到根据。他就到网上查,说在《大清全典》里面有,其实根本没有《大清全典》,网上乱写的,是《大清会典》。我们的编辑又到上海图书馆去查《大清会典》,《大清会典》是分上下册的,我们要找的内容在下册,而上海图书馆只有上册、没有下册。怎么办?再找,最后找到《清史稿》,总算查清楚了。历来祭祀都是一个大事情,清朝的时候,不同的祭祀要穿不同的衣服:祭老祖宗穿黄衣服,黄色代表我们民族;祭天穿蓝衣服,天空是蓝的;祭日穿红衣服;祭月穿白衣服。这篇文章原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用字差错,现在把清代祭祀的内容加进去,文章的知识含量就丰富了,通过内容饱满度来提高刊物的质量。
“桃李满天下”的意思,大家都是知道的;词典上面也有“桃李”的解释,但这是源自一个很生动的典故,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我们曾经收到一篇来稿,专门谈为什么称学生为“桃李”。来稿开篇就讲有一个人叫子贡,他培养了很多人,提拔了很多人,但当他受到魏国的魏文侯的迫害时,没有一个学生出来为他讲话,所以他非常伤心地逃出魏国了。这篇文章就是这么开头的,审稿编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个疑问,子贡不是孔夫子的学生吗?怎么会到魏文侯那里去呢?他做官的话,也不应该在魏国,应该在鲁国啊。马上把稿子送我们的编委金文明把关。一查,不是子贡,是子质。子贡是春秋时代的,子质是战国时代的,不同时代的两个人。子质才是魏国的大臣,培养了很多人,最后受到迫害,人家都不帮他,逃到赵国去了。他向赵国的国君诉苦,你看我培养了那么多学生,最后都不帮我。赵国的国君就给他打了一个比喻,培养学生就好像栽培树木,要看你栽培的是什么树木,栽一棵果树,夏天可以乘凉,秋天可以吃果子,如果你栽一棵荆棘,就会长出刺来刺你。后来就把培养学生称为“十年树木”,把好的学生比作“桃李”,“桃李满天下”就是从这儿来的。我们通过编委把关,质量就有了保证。“以质为魂”,是我们的一项传统。

▲《咬文嚼字》获2017年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
“以用为上”,就是强调实用。办刊物当然要讲可读性,但我们说可用性比可读性更重要。人家看你的刊物不是看着好玩的,是想看了要有用的,所以要以用为上。每一篇文章的取舍,要把实用性作为判断稿件的一个标准,想想有多少人会碰到这个问题,要抓那种用途最大的话题来做文章。我们提出按照话题的热度来选取稿件,什么是最好的稿件呢?就是有聚焦点的稿件,这个话题可以聚焦,全社会都在关注的,大家都用得到的。没有聚焦点的话,就抓兴奋点,只要你提出来读者就会感兴趣的。兴奋点也没找到的话,最低的底线叫共同点,是我们的七类读者在工作中都会碰到的,这就是共同点,这是一个底线。有一年我们出去讲课,到处有人在问,“唯一”的“唯”,你说是“口字旁”还是“竖心旁”。你要查词典的话,各说各的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竖心旁”,《汉语大词典》则以“口字旁”为主。读者急需解决这个问题,怎么办?我们想不管花多少力量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因为这是一个实用性的话题。我们组织了三个专家组,分头在那研究。三个专家组的意见一汇总,非常统一。唯一的“唯”,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,使用中有一个变化过程,开始是三个字,“口字旁”“竖心”“绞丝旁”,都可以用于“唯一”,先秦的古籍当中,这三个字都在用;到了汉代变成两个,绞丝旁没有了;到了宋代以后,一会儿是“竖心旁”占上风,一会儿是“口字旁”占上风,在拉锯;到了“五四”以后,口字旁占绝对的优势;新中国建立以后,“口字旁”一统天下,“竖心旁”是不用的。现在怎么会提出“竖心旁”呢?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编撰者考虑到历史上有一千多年的时间用过“竖心旁”,为了跟历史接轨又恢复了“竖心旁”的用法。所以接受过语文教育的人都习惯用“口字旁”,不习惯“竖心旁”。我们把三个专家组的意见公布出去,得到了全国新闻出版同仁的一致赞成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应该是从善如流吧,从第五版起改成了“口字旁”,采纳了我们的意见。我觉得这就是“以用为上”的办刊方针,我们的刊物有这一种精神,在社会上面可以产生它的影响。
第四条办刊方针叫“以学为根”。语言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,我们刊发的文章,表面看上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,但一定是以语言学作为它的基础,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凭自己个人的用字习惯在说话,那样你是办不好刊物的。我们整个刊物的基础是语言学、文字学、修辞学、音韵学。编辑部的人,看上去搞的是非常实用的东西,但你的根基都是一门科学,任何语言现象,最后都要在这门科学上面找到根据,否则你的刊物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。所以现在他们经常在研究一些课题,让自己能够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比如“七月流火”的原意是天气转凉,但在我们当代生活中,“七月流火”是指天气炎热,这就是语义转移。这是一种语言现象,到底转移得对还是错,你要回答这个问题。还有我们现在经常讲的“问鼎冠军”,这个“问鼎”到底是拿到冠军还是没拿到冠军?古人是指没有拿到冠军,但是有机会去拿这个鼎,“问鼎”,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用作获得冠军,跟过去的意思不一样了。你说“固步自封”,过去我们是用“故事”的“故”,现在写成“巩固”的“固”;莫名其妙,过去是“姓名”的“名”,现在很多人写成“光明”的“明”。这样的语言现象很多,这种现象在语言学当中称之为变异。有的是读音变,比如过去我们讲“叶(shè)公好龙”,现在是“叶(yè)公好龙”。语言学的这种变异分两类,一类叫积极变异,一类叫消极变异。积极变异是语言的发展,消极变异是语言的失范,是偏离规范的。对于积极变异,语文刊物要推动,要引导读者学会正确运用;对于消极变异,你要批评,要告诉社会什么是正确的。关键问题就是要判断什么是积极变异、什么是消极变异,心中要有底,心里没有学问的基础,判断稿子时,你的底气是不足的,所以我说要“以学为根”。

▲郝铭鉴(前排坐者中)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员工合影(2005年)
对于语言变异现象,我们讨论下来归纳为三大要素:首先要有必要性,如果现实表达有需要,就是说明它有内驱力推动着变化;第二个是合理性,变了以后是不是符合汉语的结构规律,不要变出一个“四不像”,汉语根本不能接受,那也不行;第三个是稳定性,就是今天这样变了,明天还可以用,后天还可以,最后成为一种大家接受的新的语言材料。符合这三条,我们认为就是积极变异;即使跟过去不一样,也是可以接受的。“艾滋病”,过去我们用“爱情”的“爱”,现在用“草头艾”,这个都是变异现象。类似这种情况,都是要求编辑部的成员有语言学科的学术背景,所以要“以学为根”。
我们的十六字方针:“以人为本,以质为魂,以用为上,以学为根。”掌握这十六个字,贯彻这十六个字,刊物才有生命力,在读者当中才有信誉。没有一个读者对刊物是忠诚的,因为他都是根据自己的切身需要来选择的,只要不符合需要,就会随时离开。但是《咬文嚼字》的读者忠诚度是很高的,就和这十六字办刊方针有关,因为读者从这本刊物当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